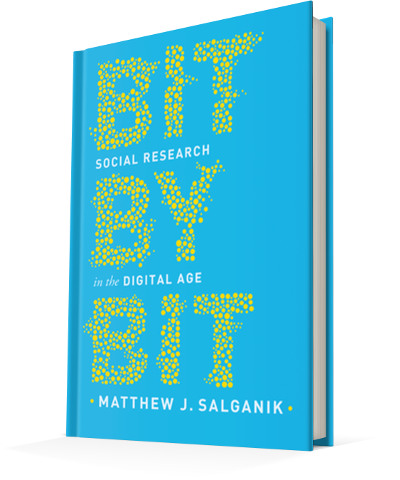歷史附錄
這個歷史附錄簡要回顧了美國的研究倫理。
任何關於研究倫理的討論都需要承認,在過去,研究人員以科學的名義做了可怕的事情。其中最糟糕的是Tuskegee梅毒研究(表6.4)。 1932年,美國公共衛生署(PHS)的研究人員在一項研究中招募了約400名感染梅毒的黑人,以監測該疾病的影響。這些人是從阿拉巴馬州塔斯基吉附近地區招募來的。從一開始,該研究是非治療性的;它的目的僅僅是記錄黑人男性的疾病史。參與者被欺騙了研究的性質 - 他們被告知這是一項關於“壞血”的研究 - 他們被提供虛假和無效的治療,即使梅毒是一種致命的疾病。隨著研究的進展,開發了安全有效的梅毒治療方法,但研究人員積極介入,以防止參與者在其他地方接受治療。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研究小組為研究中的所有男子確定了延期草案,以防止男性在進入武裝部隊時得到的待遇。研究人員繼續欺騙參與者並拒絕他們關心40年。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是在當時美國南部常見的種族主義和極端不平等的背景下進行的。但是,在其40年的歷史中,該研究涉及數十名黑人和白人研究人員。而且,除了直接參與的研究人員之外,還有許多人必須閱讀醫學文獻中發表的15項報告中的一篇(Heller 1972)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 - 研究開始後大約30年 - 一位名叫羅伯特·巴克斯頓的小靈通員工開始在小靈通內推動這項研究,他認為這種研究在道德上是無恥的。為響應Buxtun,在1969年,小靈通召集了一個小組,對該研究進行了完整的倫理審查。令人震驚的是,倫理審查小組決定研究人員應繼續拒絕接受受感染男性的治療。在審議過程中,小組的一名成員甚至評論說:“你永遠不會再有這樣的研究;利用它“ (Brandt 1978) 。全白小組(主要由醫生組成)確實決定應該獲得某種形式的知情同意。但該小組認為,由於年齡和教育水平低,男性本身無法提供知情同意。因此,專家組建議研究人員從當地醫療官員那裡獲得“代理知情同意書”。因此,即使經過全面的倫理審查,仍然會繼續保留醫療服務。最終,Buxtun將這個故事帶給了一名記者,並且在1972年,Jean Heller撰寫了一系列報紙文章,將這項研究暴露給了全世界。只是在廣泛的公眾憤慨之後,這項研究才最終結束,並為那些倖存下來的人提供了照顧。
| 日期 | 事件 |
|---|---|
| 1932年 | 大約400名患有梅毒的男性參加了這項研究;他們沒有被告知研究的性質 |
| 1937-38 | PHS向該地區發送移動治療單位,但對研究中的男性進行治療 |
| 1942-43 | 為了防止研究中的男性接受治療,PHS進行干預以防止他們被選中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
| 20世紀50年代 | 青黴素成為梅毒的廣泛可用和有效的治療方法;研究中的男性仍未得到治療(Brandt 1978) |
| 1969年 | 小靈通召集了對該研究的倫理審查;專家組建議繼續研究 |
| 1972年 | 前PHS員工Peter Buxtun告訴記者這項研究,媒體打破了這個故事 |
| 1972年 | 美國參議院舉行人體實驗聽證會,包括塔斯基吉研究 |
| 1973年 | 政府正式結束研究並授權對倖存者進行治療 |
| 1997年 | 美國總統克林頓公開並正式為塔斯基吉研究道歉 |
這項研究的受害者不僅包括399名男性,還包括他們的家庭:至少22名妻子,17名兒童和2名患有梅毒的孫子女可能因為停止治療而感染了這種疾病(Yoon 1997) 。此外,該研究造成的危害在結束後很長時間內持續了很長時間。這項研究合理地減少了非洲裔美國人對醫學界的信任,信任受到侵蝕,可能導致非洲裔美國人避免醫療而損害他們的健康(Alsan and Wanamaker 2016) 。此外,缺乏信任阻礙了1980年代和90年代治療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努力(Jones 1993, chap. 14) 。
雖然這是很難想像的研究,所以今天可怕的情況發生,我認為有從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三個重要教訓人進行了數字化時代的社會研究。首先,它提醒我們,有一些研究認為根本不應該發生的。其次,它向我們展示了這一研究已經完成研究後,會損害不僅僅是參與者,而且他們的家庭和整個社區長。最後,它表明,研究人員可以做出可怕的道德決策。事實上,我認為它應該引起研究者有些害怕今天有這麼多的人參與到這項研究中取得了時間這麼長時間的這種可怕的決定。而且,不幸的是,塔斯基吉絕不是唯一的;有問題的社會和醫學研究的其他幾個例子在這個時代(Katz, Capron, and Glass 1972; Emanuel et al. 2008)
1974年,為響應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和研究人員的其他道德失敗,美國國會成立了國家生物醫學和行為研究人類受試者保護委員會,並責成其製定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的倫理準則。在貝爾蒙特會議中心舉行了四年的會議後,該小組編寫了貝爾蒙特報告 ,該報告對生物倫理學和日常研究實踐中的抽象辯論產生了巨大影響。
貝爾蒙特報告有三個部分。在實踐與研究之間的第一個邊界 - 報告闡述了它的範圍。特別是,它主張區分尋求普遍知識的研究和包括日常治療和活動在內的實踐 。此外,它認為貝爾蒙特報告的道德原則僅適用於研究。有人認為,研究與實踐之間的區別是貝爾蒙特報告不適合數字時代社會研究的一種方式(Metcalf and Crawford 2016; boyd 2016) 。
貝爾蒙特報告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列出了三項道德原則 - 尊重人;善行;和正義 - 並描述這些原則如何應用於研究實踐。這些是我在本章正文中更詳細描述的原則。
貝爾蒙特報告設定了廣泛的目標,但它不是一個可以輕鬆用於監督日常活動的文件。因此,美國政府制定了一套俗稱共同規則的法規 (其正式名稱為聯邦法規第45號標準,第46部分,AD子部分) (Porter and Koski 2008) 。這些法規描述了審查,批准和監督研究的過程,它們是機構審查委員會(IRB)負責執行的法規。要了解貝爾蒙特報告和共同規則之間的區別,請考慮每個報告如何討論知情同意:貝爾蒙特報告描述了知情同意的哲學原因和代表真正知情同意的廣泛特徵,而共同規則列出了所需的八個和六個知情同意文件的可選要素。根據法律,共同規則幾乎涵蓋了從美國政府獲得資金的所有研究。此外,許多從美國政府獲得資金的機構通常將共同規則應用於該機構發生的所有研究,無論資金來源如何。但共同規則不會自動適用於未從美國政府獲得研究經費的公司。
我認為幾乎所有的研究人員都尊重貝爾蒙特報告中所表達的道德研究的廣泛目標,但是共同規則和與IRB合作的過程普遍存在煩惱(Schrag 2010, 2011; Hoonaard 2011; Klitzman 2015; King and Sands 2015; Schneider 2015) 。要明確的是,批評IRB的人並不反對道德規範。相反,他們認為當前的系統沒有達到適當的平衡,或者它可以通過其他方法更好地實現其目標。但是,我將把這些IRB視為給定的。如果您需要遵守IRB的規則,那麼您應該這樣做。不過,我建議你考慮你的研究的倫理時也採取以原則為基礎的方法。
這個背景非常簡要地總結了我們如何在美國達到基於規則的IRB審查制度。在考慮今天的貝爾蒙特報告和共同規則時,我們應該記住,它們是在不同的時代創造的,並且非常明智地回應那個時代的問題,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的醫學倫理違規(Beauchamp 2011) 。
除了醫學和行為科學家為創建道德準則所做的努力之外,計算機科學家還有一些規模較小且知名度較低的工作。事實上,第一批遇到數字時代研究所帶來的倫理挑戰的研究人員並不是社會科學家:他們是計算機科學家,特別是計算機安全領域的研究人員。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計算機安全研究人員進行了許多有道德問題的研究,涉及接管殭屍網絡和黑客攻擊數千台密碼較弱的計算機(Bailey, Dittrich, and Kenneally 2013; Dittrich, Carpenter, and Karir 2015) 。為了回應這些研究,美國政府 - 特別是國土安全部 - 創建了一個藍帶委員會,為涉及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的研究撰寫指導性道德框架。這項努力的結果是Menlo報告 (Dittrich, Kenneally, and others 2011) 。儘管計算機安全研究人員的關注點與社會研究人員的關注點並不完全相同,但“門洛報告”為社會研究人員提供了三個重要的經驗教訓。
首先,“門洛報告”重申了貝爾蒙特的三項原則 - 尊重人,受益和正義 - 並增加了第四項: 尊重法律和公共利益 。我在本章正文(第6.4.4節)中描述了這第四項原則以及它應如何應用於社會研究。
其次,“門洛報告”呼籲研究人員超越“貝爾蒙特報告”中關於“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這一狹隘定義,轉向更為籠統的“人類傷害研究”概念。貝爾蒙特報告範圍的局限性是Encore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普林斯頓大學和佐治亞理工學院的IRB裁定Encore不是“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因此不受共同規則的審查。然而,Encore顯然具有人類傷害的潛力;在極端情況下,Encore可能會導致無辜的人被鎮壓政府監禁。基於原則的方法意味著即使IRB允許,研究人員也不應躲在“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的狹隘的法律定義背後。相反,他們應該採用更為籠統的“具有人類傷害潛力的研究”的概念,並且他們應該將自己的所有研究都置於道德考慮的人類傷害潛力之下。
第三,“門洛報告”呼籲研究人員擴大在應用貝爾蒙特原則時考慮的利益相關者。隨著研究從單獨的生活領域轉移到更加嵌入日常活動的領域,必須擴展道德考慮,而不僅僅是特定的研究參與者,包括非參與者和研究所在的環境。換句話說,“門洛報告”要求研究人員擴大他們的道德視野,而不僅僅是他們的參與者。
本歷史附錄簡要回顧了社會科學和醫學科學以及計算機科學中的研究倫理。對於醫學科學研究倫理的書籍處理,參見Emanuel et al. (2008)或Beauchamp and Childress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