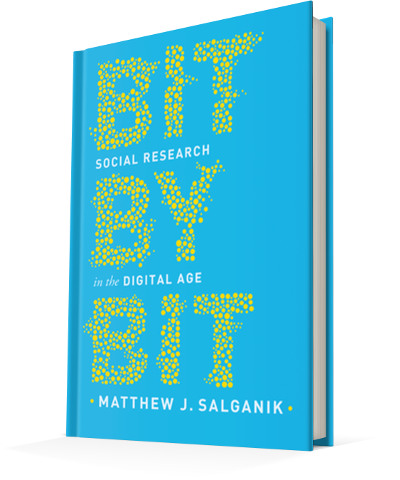活動
- 難度:容易
,中等
,很難
, 很難
- 需要數學(
)
- 需要編碼(
)
- 數據採集 (
)
- 我最喜歡的 (
)
-
[
]在反對情緒傳染實驗時, Kleinsman and Buckley (2015)寫道:
“即使Facebook實驗的風險確實很低,即使事後看來結果被認為是有用的,但仍有一個重要原則必須堅持。無論涉及多少金額,偷竊都是偷竊的,所以無論研究的性質如何,我們都有權在沒有我們的知識和同意的情況下進行實驗。“
- 本章討論的兩個倫理框架中的哪一個 - 結果主義或義務論 - 這個論點最明顯地與之相關?
- 現在,想像一下你想反對這個立場。你如何向紐約時報的記者辯論?
- 如果你和同事討論這個問題,你的論點怎麼會有所不同呢?
-
[
] Maddock, Mason, and Starbird (2015)考慮了研究人員是否應該使用已被刪除的推文的問題。閱讀他們的論文以了解背景知識。
- 從道義論的角度分析這個決定。
- 從結果主義的角度分析完全相同的決定。
- 在這種情況下你覺得哪個更有說服力?
-
[
]在一篇關於田間試驗倫理學的文章中, Humphreys (2015)提出了以下假設性實驗,以強調未經所有受影響方同意而乾擾某些並幫助他人的干預的倫理挑戰。
“一位社區組織聯繫研究人員,想要弄清楚在貧民窟設置路燈是否會減少暴力犯罪。在這項研究中,受試者是罪犯:尋求犯罪分子的知情同意可能會損害研究,並且無論如何都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違反對人的尊重);犯罪分子可能會承擔研究的費用而不會受益(違反正義);關於研究的好處會有分歧 - 如果它有效,犯罪分子特別不會重視它(產生評估仁慈的難度)......這裡的特殊問題不僅僅圍繞著主題。如果例如犯罪分子對組織燈具進行報復,那麼在這裡也存在獲得非主體的風險。該組織可能非常清楚這些風險,但願意承擔這些風險,因為他們錯誤地相信富裕大學的研究人員沒有根據的期望,而富裕大學本身也是出版的動機。
- 寫一封電子郵件給社區組織,按照設計提供您對實驗的道德評估?你會幫他們按照建議進行實驗嗎?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您的決定?
- 是否有一些變化可能會改善您對此實驗設計的道德規範的評估。
-
[
]在20世紀70年代,60名男性參加了在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學的男士浴室進行的實地實驗(研究人員沒有(Middlemist, Knowles, and Matter 1976)大學名稱) (Middlemist, Knowles, and Matter 1976) 。研究人員對人們如何應對違反個人空間的行為感興趣, Sommer (1969)其定義為“圍繞一個人身體的無形邊界區域,入侵者可能無法進入該區域。”更具體地說,研究人員選擇研究如何男人的排尿受到附近其他人的影響。在進行了一項純粹的觀察性研究後,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實地試驗。參與者被迫使用三個小便池中最左邊的小便池(研究人員沒有詳細解釋這是怎麼做的)。接下來,參與者被分配到三個人際距離中的一個。對於一些男人來說,一個同盟者在他們旁邊使用了一個小便池;對於一些男人來說,一個同盟者使用了一個距離他們一個小便池的小便池;對於一些男人來說,沒有同盟者進入浴室。研究人員測量了他們的結果變量 - 延遲時間和持久性 - 將研究助理安置在參與者小便池附近的廁所內。以下是研究人員描述測量程序的方法:
“一名觀察員駐紮在緊鄰受試者小便池的廁所內。在對這些程序進行試驗性測試期間,很明顯聽覺提示不能用於表示[排尿]的開始和停止......相反,使用了視覺提示。觀察者使用了一個嵌入在廁所地板上的一摞書中的periscopic棱鏡。地板和馬桶隔間之間有一個11英寸(28厘米)的空間,通過潛望鏡可以看到使用者下半身的視野,並可以直接目視觀察尿流。然而,觀察者無法看到主體的臉。當一名受試者上升到小便池時,觀察者開始兩次秒錶,當小便開始時停止一次,並在排尿結束時停止另一次。
研究人員發現,物理距離的減少會導致發病延遲增加和持續性降低(圖6.7)。
- 您是否認為參與者受到此實驗的傷害?
- 你認為研究人員應該進行這項實驗嗎?
- 如果有的話,您會建議改變道德平衡嗎?

圖6.7: Middlemist, Knowles, and Matter (1976) 。進入浴室的男性被分配到三個條件中的一個:近距離(一個同盟者被放置在緊鄰的小便池中),中等距離(一個同盟者被放置一個小便池)或對照(沒有同盟者)。駐守在廁所的一名觀察員使用定制的潛望鏡來觀察和計算排尿的延遲和持續時間。估算值附近的標準誤差不可用。改編自Middlemist, Knowles, and Matter (1976) ,圖1。
-
[
,
] 2006年8月,在初選前大約10天,居住在密歇根州的2萬人收到了一封郵件,顯示了他們的投票行為和鄰居的投票行為(圖6.8)。 (正如本章所述,在美國,州政府會記錄每次選舉中誰投票,這些信息可供公眾查閱。)一件郵件通常會使選民投票率增加約一個百分點,但這一次增加了投票率達到8.1個百分點,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影響(Gerber, Green, and Larimer 2008) 。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一位名叫Hal Malchow的政治人員向唐納德·格林提供了10萬美元,而不是公佈實驗結果(可能是因為Malchow可以自己利用這些信息) (Issenberg 2012, p 304) 。但是,Alan Gerber,Donald Green和Christopher Larimer確實在2008年的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中發表了這篇論文。
當您仔細檢查圖6.8中的郵件時,您可能會注意到研究人員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它上面。相反,返回地址是實用政治諮詢。在對該論文的承認中,作者解釋說:“特別感謝實用政治諮詢公司的Mark Grebner,他設計並管理了這裡研究的郵件程序。”
- 根據本章所述的四個道德原則評估此治療的使用。
- 根據情境完整性的概念評估治療。
- 如果有的話,您會推薦哪些更改?
- 如果Mark Grebner此時已發出類似的郵件,是否會影響您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更一般地說,研究人員應該如何考慮評估從業者創造的現有乾預措施?
- 想像一下,您決定嘗試接受治療組患者的知情同意,但不會接受對照組患者的知情同意。這一決定對您理解治療組和對照組之間投票率差異的原因有何影響?
- 寫一篇道德附錄,該論文在發表時可能與本文一起出現。

圖6.8:來自Gerber, Green, and Larimer (2008)鄰居郵件程序Gerber, Green, and Larimer (2008) 。該郵件將投票率提高了8.1個百分點,這是單件郵件所觀察到的最大影響。經Gerber, Green, and Larimer (2008)許可轉載,附錄A.
-
[
]這建立在前一個問題的基礎上。一旦這些20,000封郵件被發送(圖6.8),以及60,000個其他可能不那麼敏感的郵件程序,參與者就會產生強烈反對。事實上, Issenberg (2012) (p.198)報導說“Grebner [實用政治諮詢主管]從來沒有能夠計算出有多少人通過電話抱怨這個問題,因為他的辦公室電話答錄機充滿了新的呼叫者無法留言。“事實上,格雷布納指出,如果他們擴大治療範圍,反彈可能會更大。他對其中一位研究人員艾倫·格伯說:“艾倫,如果我們花了五十萬美元,覆蓋了整個州,你和(Issenberg 2012, 200)一起生活。” (Issenberg 2012, 200)
- 此信息是否會改變您對上一個問題的回答?
- 面對不確定性處理決策的策略,您會建議將來進行類似的研究嗎?
[
,
]在實踐中,大多數倫理辯論都發生在研究人員沒有得到參與者真正知情同意的研究中(例如,本章所述的三個案例研究)。但是,對於具有真正知情同意的研究,也可能出現倫理爭論。設計一個假設的研究,你會得到參與者的真正知情同意,但你仍然認為這是不道德的。 (提示:如果你正在努力,你可以嘗試閱讀Emanuel, Wendler, and Grady (2000) 。)
[
,
研究人員經常難以向對方和公眾描述他們的道德思想。在發現Tastes,Ties和Time被重新識別後,研究團隊的負責人Jason Kauffman就該項目的道德規範發表了一些公開評論。閱讀Zimmer (2010) ,然後使用本章中描述的原則和道德框架重寫Kauffman的評論。
-
[
Banksy是英國最著名的當代藝術家之一,以政治導向的街頭塗鴉而聞名(圖6.9)。然而,他的確切身份是一個謎。 Banksy有一個個人網站,所以如果他願意,他可以公開他的身份,但他選擇不這樣做。 2008年,“ 每日郵報”發表了一篇聲稱能識別出Banksy真名的文章。然後,在2016年,Michelle Hauge,Mark Stevenson,D。Kim Rossmo和Steven C. Le Comber (2016)嘗試使用地理剖析的Dirichlet過程混合模型來驗證這一主張。更具體地說,他們收集了Banksy在布里斯托爾和倫敦的公共塗鴉的地理位置。接下來,通過搜索舊的報紙文章和公共投票記錄,他們找到了指定個人,他的妻子和他的足球(即足球)隊的過去地址。作者總結了他們論文的發現如下:
“沒有其他嚴重的'嫌疑人'[原文如此]進行調查,根據此處提供的分析,很難對Banksy的身份做出結論性陳述,除了說布里斯托爾和倫敦的地緣信息高峰包括已知相關的地址[名稱編輯]。“
在Metcalf and Crawford (2016)之後,我更詳細地考慮了這個案例,我決定在討論這項研究時不要包括個人的名字。
- 使用本章中的原則和道德框架評估本研究。
- 你做完這項研究嗎?
- 作者在其論文的摘要中用以下句子證明了這項研究的合理性:“更廣泛地說,這些結果支持以前的建議,即對較小的恐怖主義相關行為(例如塗鴉)的分析可以用來幫助找到更嚴重的恐怖主義基地事件發生了,並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說明模型應用於一個複雜的,現實世界的問題。“這會改變你對論文的看法嗎?如果是這樣,怎麼樣?
- 作者在他們的論文末尾包括以下道德註釋:“作者知道並尊重[編輯名稱]及其親屬的隱私,因此僅使用公共領域的數據。我們故意省略了精確的地址。“這會改變你對論文的看法嗎?如果是這樣,怎麼樣?在這種情況下,你認為公共/私人二分法是否有意義?

圖6.9:Banksy在英國切爾滕納姆的間諜展位照片,作者:Kathryn Yengel,2014年。資料來源:Kathryn Yengel / Flickr 。
-
[
Metcalf (2016)認為“包含私人數據的公開數據集是研究人員最感興趣的,對受試者來說風險最大。”
- 支持這種說法的兩個具體例子是什麼?
- 在同一篇文章中,Metcalf還聲稱,假設“任何信息損害已經由公共數據集完成,這是不合時宜的。”舉一個例子說明情況可能如此。
-
[
,
]在本章中,我提出了一條經驗法則,即所有數據都是可識別的, 所有數據都可能具有敏感性。表6.5提供了一些數據示例列表,這些數據沒有明顯的個人識別信息,但仍然可以鏈接到特定的人。
- 選擇其中兩個示例並描述兩種情況下的重新識別攻擊如何具有相似的結構。
- 對於(a)部分中的兩個示例中的每一個,描述數據如何揭示有關數據集中人員的敏感信息。
- 現在從表中選擇第三個數據集。給考慮發布它的人寫一封電子郵件。向他們解釋這些數據如何可能被識別並且可能是敏感的。
表6.5:沒有任何明顯的個人識別信息但仍可與特定人員相關聯的社交數據示例 數據 參考 健康保險記錄 Sweeney (2002) 信用卡交易數據 Montjoye et al. (2015) Netflix電影評級數據 Narayanan and Shmatikov (2008) 電話元數據 Mayer, Mutchler, and Mitchell (2016) 搜索日誌數據 Barbaro and Zeller (2006) 有關學生的人口統計,行政和社會數據 Zimmer (2010) -
[
把自己放在每個人的角度包括你的參與者和普通大眾,而不僅僅是你的同行。這種區別在猶太慢性病醫院(Katz, Capron, and Glass 1972, chap. 1; Lerner 2004; Arras 2008)的案例中有所說明。
Chester M. Southam博士是斯隆 - 凱特琳癌症研究所的傑出醫生和研究員,以及康奈爾大學醫學院的醫學副教授。 1963年7月16日,Southam和兩位同事將活癌細胞注入紐約猶太人慢性病醫院22名虛弱患者的屍體中。這些注射是Southam研究癌症患者免疫系統的一部分。在早期的研究中,Southam發現健康的志願者能夠在大約四到六週內拒絕注射癌細胞,而患癌症的患者則需要更長時間。 Southam想知道癌症患者的延遲反應是因為他們患有癌症,還是因為他們是老年人並且已經衰弱。為了解決這些可能性,Southam決定將活癌細胞注射到一群年老和虛弱但沒有患癌症的人群中。當研究的消息傳播,部分是由於被要求參加的三位醫生的辭職所引發的,一些人與納粹集中營實驗進行了比較,但其他人 - 部分基於Southam的保證 - 發現研究沒有問題。最終,紐約州董事會審查了該案件,以決定Southam是否應該能夠繼續從事醫學。 Southam在辯護中辯稱,他的行為是“負責臨床實踐的最佳傳統。”他的辯護基於一些主張,這些主張都得到了幾位傑出專家的支持:(1)他的研究是具有很高的科學和社會價值; (2)參與者沒有明顯的風險; Southam 10年以上經驗的部分內容,涉及600多個科目; (3)應根據研究人員提出的風險程度調整披露水平; (4)該研究符合當時的醫療實踐標準。最終,攝政王的董事會發現Southam犯有欺詐,欺騙和不專業的行為,並暫停了他的醫療執照一年。然而,僅僅幾年後,Southam當選美國癌症研究協會主席。
- 使用本章中的四個原則評估Southam的研究。
- Southam似乎從同事的角度出發,正確地預測了他們如何回應他的工作;事實上,他們中的許多人代表他作證。但他無法或不願意了解他的研究如何令公眾感到不安。您認為公眾輿論在研究倫理方面應該具有什麼樣的作用 - 這可能與參與者或同行的觀點截然不同?如果民意和同行意見不同,會發生什麼?
[
在題為“剛果東部的人群播種:使用手機實時收集衝突事件數據”的論文中,Van der Windt和Humphreys (2016)描述了他們在剛果東部創建的分佈式數據收集系統(見第5章)。描述研究人員如何處理對參與者可能造成傷害的不確定性。
-
[
] 2014年10月,三位政治科學家向蒙大拿州的102,780名登記選民發送了郵件 - 約佔該州登記選民的15% (Willis 2014) - 這是衡量獲得更多信息的選民是否更有可能投票的實驗的一部分。郵件被標記為“2014蒙大拿州大選選民信息指南” - 蒙大拿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在一個無黨派選舉中,從自由派到保守派,包括巴拉克奧巴馬和米特羅姆尼作為比較。郵寄者還包括蒙大拿州大印章的複製品(圖6.10)。
郵件引起蒙大拿州選民的投訴,他們讓蒙大拿州的國務卿琳達麥卡洛克向蒙大拿州政府提出正式投訴。僱用研究人員的大學 - 達特茅斯和斯坦福 - 給收到郵件的每個人發了一封信,為任何可能的混淆道歉,並明確表示郵件“不隸屬於任何政黨,候選人或組織,並且不打算影響任何種族。“這封信還澄清了排名”依賴於有關誰捐贈給每個活動的公共信息“(圖6.11)。
2015年5月,蒙大拿州政治實踐專員Jonathan Motl確定研究人員違反了蒙大拿州的法律:“專員確定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斯坦福,達特茅斯和/或其研究人員違反了蒙大拿州的競選活動執行法律要求註冊,報告和披露獨立支出“( Motl (2015)充分調查結果3)。專員還建議縣檢察官調查未經授權使用蒙大拿州大印章是否違反蒙大拿州法律(Motl 2015) 。
斯坦福和達特茅斯不同意Motl的裁決。一位名叫Lisa Lapin的斯坦福女發言人說:“斯坦福......不相信任何選舉法都受到了侵犯”,而且郵件“並不包含支持或反對任何候選人的任何支持。”她指出郵件明確表示它“是無黨派的,不支持任何候選人或政黨“ (Richman 2015) 。
- 使用本章中描述的四個原則和兩個框架評估本研究。
- 假設郵寄者被隨機抽取選民樣本(但稍後會更多關於這一點),這種郵件在什麼條件下可能會改變最高法院大法官選舉的結果?
- 實際上,郵寄者並未隨機抽取選民樣本。根據傑里米約翰遜(一位協助調查的政治科學家)的報告,郵件“被發送給64,265名選民,這些選民被認為可能是民主黨傾向於民主黨傾向的區域,並且共有39,515名選民被認定為共和黨傾斜區域的中間派保守派。研究人員證明了民主黨和共和黨人之間的差距是合理的,理由是他們預計民主黨選民的投票率將大大降低。“這是否會改變你對研究設計的評估?如果是這樣,怎麼樣?
- 在回應調查時,研究人員表示他們選擇這次選舉的部分原因是“司法競選在初選中都沒有受到激烈的爭議。根據對前蒙大拿州司法選舉背景下2014年初選結果的分析,研究人員確定所設計的研究報告不會改變任何一項競賽的結果“ (Motl 2015) 。這是否會改變您對研究的評估?如果是這樣,怎麼樣?
- 事實上,選舉結果並不是特別接近(表6.6)。這是否會改變您對研究的評估?如果是這樣,怎麼樣?
- 事實證明,一項研究人員向達特茅斯IRB提交了一項研究,但其細節與蒙大拿州實際研究的細節大不相同。蒙大拿州使用的郵件從未提交給IRB。該研究從未提交給斯坦福大學IRB。這是否會改變您對研究的評估?如果是這樣,怎麼樣?
- 事實證明,研究人員向加利福尼亞州的143,000名選民和新罕布什爾州的66,000名選民發送了類似的選舉材料。據我所知,這些大約200,000封郵件沒有引發正式投訴。這是否會改變您對研究的評估?如果是這樣,怎麼樣?
- 如果你是主要的調查員,你會做什麼,如果有的話?如果您有興趣探索是否有其他信息可以增加無黨派競選中的選民投票率,您將如何設計該研究?
表6。6:2014年蒙大拿州最高法院大法官選舉結果(來源:蒙大拿州國務卿網頁) 候選人 收到投票 百分比 最高法院大法官#1 W.大衛赫伯特 65404 21.59% 吉姆賴斯 236963 78.22% 最高法院大法官#2 勞倫斯範戴克 134904 40.80% 邁克麥 195303 59.06% 
圖6.10:三名政治科學家向蒙大拿州的102,780名登記選民發送郵件,作為衡量獲得更多信息的選民是否更有可能投票的實驗的一部分。該實驗的樣本量約佔該州合格選民的15% (Willis 2014) 。轉載自Motl (2015) 。

圖6.11:發送給蒙大拿州102,780名登記選民的道歉信,他們收到了圖6.10所示的郵件。這封信是由達特茅斯總統和斯坦福大學發出的,這些大學聘請了派出郵件的研究人員。轉載自Motl (2015) 。
-
[
] 2016年5月8日,兩位研究人員-Emil Kirkegaard和Julius Bjerrekaer從在線約會網站OkCupid上刪除了信息,公開發布了大約70,000名用戶的數據集,包括用戶名,年齡,性別,地點,宗教相關意見等變量,占星術相關的意見,約會興趣,照片數量等,以及對網站上的前2,600個問題的答案。在隨附發布的數據的一份草案中,作者表示“有些人可能會反對收集和發布這些數據的道德規範。但是,數據集中找到的所有數據已經或者已經公開可用,因此發布此數據集只是以更有用的形式呈現。“
為響應數據發布,其中一位作者在Twitter上被問到:“這個數據集具有高度可重新識別性。甚至包括用戶名?完成任何工作是為了匿名化嗎?“他的回答是”不是。數據已經公開。“ (Zimmer 2016; Resnick 2016) 。
- 使用本章中討論的原則和道德框架評估此數據發布。
- 您會將這些數據用於自己的研究嗎?
- 如果你自己刮掉它會怎麼樣?
-
[
] 2010年,美國陸軍情報分析員向維基解密組織提供了25萬條機密外交電報,隨後在線發布。 Gill and Spirling (2015)認為“維基解密的披露可能代表了Gill and Spirling (2015)數據,可能被用來測試國際關係中的微妙理論”,然後在統計上描述洩露文件的樣本。例如,作者估計,在此期間,它們佔所有外交電報的5%左右,但這一比例因大使館而異(見其論文的圖1)。
- 閱讀論文,然後寫一個道德的附錄。
- 作者沒有分析任何洩露文件的內容。是否有使用這些電纜的項目?是否有任何使用這些電纜的項目你不會進行?
-
[
為了研究公司如何回應投訴,研究人員向紐約市的240家高端餐廳發送了假投訴信。這是虛構信件的摘錄。
“我正在寫這封信給你,因為我對你最近在你餐廳的經歷感到憤怒。不久前,我和妻子慶祝了我們的一周年紀念日。 ......當症狀在進食後約四小時開始出現時,晚上變得酸痛。延長的噁心,嘔吐,腹瀉和腹部絞痛都指向一件事:食物中毒。我只是覺得我們特別的浪漫之夜變成了我的妻子,看著我蜷縮在我們浴室瓷磚地板上的胎兒位置之間嘔吐,這讓我感到憤怒。 ......雖然我不打算向商業改善局或衛生部提交任何報告,但我希望你,[餐館老闆的名字]了解我所經歷的事情,期待你會做出相應的回應。“
- 使用本章中描述的原則和道德框架評估本研究。鑑於你的評估,你會做研究嗎?
- 接到這封信的餐館就是這樣的反應(Kifner 2001) :“這是烹飪混亂,因為所有者,經理和廚師通過計算機搜索[名稱編輯]預訂或信用卡記錄,審查菜單並為可能變質的食物生產交付,以及質疑廚房工人可能出現的失誤,所有這一切都受到大學和教授現在所承認的是地獄商學院研究的刺激。“這些信息會改變你對這項研究的評估嗎?
- 據我所知,這項研究未經IRB或任何其他第三方審查。這會改變您評估研究的方式嗎?為什麼或者為什麼不?
-
[
基於前一個問題,我希望您將這項研究與一項完全不同的研究進行比較,該研究也涉及餐館。在另一項研究中,Neumark及其同事(1996)派遣兩名男性和兩名女大學生用捏造的簡歷申請在費城的65家餐廳擔任服務員和女服務員,以調查餐館招聘中的性別歧視。 130份申請導致了54次訪談和39份工作機會。該研究發現了高價餐館中對女性性別歧視的統計學顯著性證據。
- 為本研究撰寫道德附錄。
- 您認為這項研究在道德上與前一個問題中描述的不同。如果是這樣,怎麼樣?
-
[
,
] 2010年左右,美國有6,548名教授收到了與此類似的電子郵件。
“親愛的Salganik教授,
我寫信給你是因為我是一名准博士。對您的研究有相當大興趣的學生。我的計劃是申請博士學位。這個即將到來的課程,我渴望在此期間盡可能多地學習研究機會。
我今天會在校園裡,雖然我知道這是短暫的通知,但我想知道你是否有10分鐘願意與我見面簡要談談你的工作以及我參與的任何可能的機會你的研究。任何方便你的時間對我都沒問題,因為在這次校園訪問期間,與你會面是我的首要任務。
提前感謝您的考慮。
真誠的,卡洛斯洛佩茲“
這些電子郵件是假的;他們是現場實驗的一部分,用於衡量教授是否更有可能對電子郵件作出回應,具體取決於(1)時間範圍(今天與下週)和(2)發送者的姓名,這些信號因種族而異。和性別(Carlos Lopez,Meredith Roberts,Raj Singh等)。研究人員發現,當要求在一周內召開會議時,高加索男性獲得教職員工的機會比女性和少數民族多25%。但是,當虛構的學生在同一天要求會議時,這些模式基本上被消除了(Milkman, Akinola, and Chugh 2012) 。
- 根據本章的原則和框架評估此實驗。
- 研究結束後,研究人員向所有參與者發送了以下簡報電子郵件。
“最近,你收到一封來自學生的電子郵件,要求你花10分鐘的時間來討論你的博士學位。程序(電子郵件的正文顯示在下面)。我們今天通過電子郵件向您匯報該電子郵件的實際目的,因為它是研究的一部分。我們真誠地希望我們的研究不會給您帶來任何干擾,如果您感到不便,我們深表歉意。我們希望這封信能夠充分解釋我們研究的目的和設計,以減輕您對參與的擔憂。如果您有興趣了解收到此消息的原因,我們想感謝您的時間和進一步閱讀。我們希望您能看到我們期望通過這項大型學術研究所產生的知識的價值。“
在解釋了研究的目的和設計後,他們進一步指出:
“一旦我們的研究結果可用,我們將在我們的網站上發布。請放心,本研究不會報告任何可識別的數據,我們的主題設計確保我們只能識別匯總的電子郵件響應模式,而不是在個人層面。在我們發布的任何研究或數據中,任何個人或大學都不會被識別。當然,任何一個單獨的電子郵件回复都沒有意義,因為個別教師可能會接受或拒絕會議請求的原因有多種。所有數據都已被去除識別,並且已從我們的數據庫和相關服務器中刪除了可識別的電子郵件回复。此外,在數據可識別的時間內,它受到強大而安全的密碼保護。正如學術界開展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一樣,我們的研究方案得到了我們大學的機構審查委員會(哥倫比亞大學Morningside IRB和賓夕法尼亞大學IRB)的批准。
如果您對作為研究對象的權利有任何疑問,您可以[編輯]或通過電子郵件[編輯]和/或賓夕法尼亞大學機構審查委員會[編輯]聯繫哥倫比亞大學晨興機構審查委員會。
再次感謝您抽出時間並了解我們正在開展的工作。“
- 在這種情況下,匯報的理由是什麼?反對的論點是什麼?您是否認為研究人員應該在這種情況下對參與者進行匯報?
- 在支持在線資料中,研究人員有一個標題為“人類受試者保護”的部分。閱讀本節。你有什麼要添加或刪除的嗎?
- 這項實驗對研究人員的成本是多少?這次實驗對參與者的成本是多少? Andrew Gelman (2010)認為,在實驗結束後,本研究的參與者可以得到補償。你同意嗎?嘗試使用本章中的原則和道德框架進行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