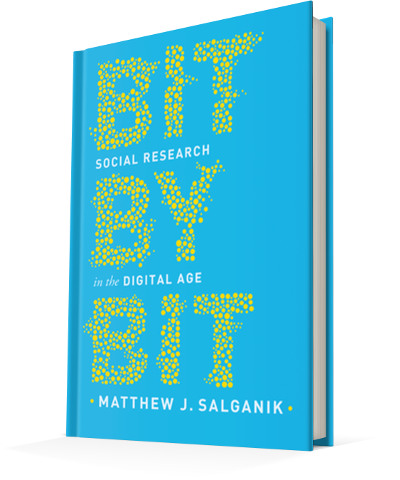6.6.1知情同意
研究人員應該,可以,也遵循以下規則:對於大多數研究某種形式的同意。
知情同意是一個基本的想法 - 有些人可能會說近乎痴迷(Emanuel, Wendler, and Grady 2000; Manson and O'Neill 2007) - 研究倫理。最簡單的研究倫理學說:“對所有事物的知情同意。”然而,這個簡單的規則與現有的道德原則,道德規範或研究實踐不一致。相反,研究人員應該,可以,並且確實遵循更複雜的規則:“對大多數研究的某種形式的同意。”
首先,為了超越關於知情同意的過於簡單化的想法,我想告訴你更多關於研究歧視的實地實驗。在這些研究中,具有不同特徵的假申請人 - 比如一些男人和一些女人 - 申請不同的工作。如果一種類型的申請人被更頻繁地僱用,那麼研究人員可以得出結論,招聘過程中可能存在歧視。就本章而言,這些實驗最重要的是這些實驗的參與者 - 雇主 - 從不提供同意。事實上,這些參與者都受到了積極的欺騙。然而,在17個國家的至少117項研究中進行了研究歧視的實地試驗(Riach and Rich 2002; Rich 2014) 。
使用實地實驗來研究歧視的研究人員已經確定了這些研究的四個特徵,這些特徵共同使他們在道德上允許:(1)對雇主的有限傷害; (2)採取可靠的歧視措施可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 (3)其他衡量歧視方法的弱點; (4)欺騙並未嚴重違反該規定的規範(Riach and Rich 2004) 。這些條件中的每一個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其中任何一個條件不滿意,那麼道德案例將更具挑戰性。其中三個特徵可以從貝爾蒙特報告中的道德原則中得出:有限的傷害(尊重人和受益)以及其他方法的巨大利益和弱點(有益和正義)。最後一個特徵,即背景規範的違反,可以從Menlo Report的法律和公共利益的尊重中得出。換句話說,就業申請是一種已經存在可能的欺騙預期的環境。因此,這些實驗不會污染已經原始的道德景觀。
除了這一基於原則的論證外,還有數十個IRB還得出結論認為,這些研究中缺乏同意符合現行規則,特別是共同規則§46.116,(d)部分。最後,美國法院還支持在實地實驗中缺乏同意和使用欺騙來衡量歧視(第81-3029號。美國上訴法院,第七巡迴法院)。因此,未經同意使用現場實驗符合現有的道德原則和現有規則(至少美國的規則)。這種推理得到了廣泛的社會研究界,數十家IRB以及美國上訴法院的支持。因此,我們必須拒絕簡單的規則“對所有事物的知情同意。”這不是研究人員遵循的規則,也不是他們應該遵循的規則。
超越“對所有事物的知情同意”使研究人員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什麼樣的研究需要哪些形式的同意?當然,圍繞這個問題存在大量爭論,儘管大部分是在模擬時代的醫學研究背景下。總結這場辯論,Nir Eyal (2012)寫道:
“越危險的介入,更多的則是高衝擊或一個明確的”關鍵生命的選擇“,更多的則是充滿價值的和有爭議的,身體的干預直接影響,越越的私人領域衝突和無人監管的實踐者,需要強大的知情同意越高。在其他場合,需要非常強大的知情同意,而事實上,對於任何形式的同意下,較小。在這些場合,成本高很容易覆蓋需求。“[引用內部排除]
這場辯論的一個重要見解是,知情同意並非全有或全無:有更強和更弱的同意形式。在某些情況下,強有力的知情同意似乎是必要的,但在其他情況下,較弱的同意形式可能是適當的。接下來,我將描述為什麼研究人員可能難以獲得知情同意的三個原因,我將在這些案例中描述一些選項。
首先,有時要求參與者提供知情同意可能會增加他們面臨的風險。例如,在Encore中,要求生活在壓制性政府下的人們同意將他們的計算機用於衡量互聯網審查,可能會使那些同意風險增加的人。當同意導致風險增加時,研究人員可以確保他們正在做的事情的信息是公開的,並且參與者可以選擇退出。此外,他們可以尋求代表參與者(例如,非政府組織)的團體的同意。
其次,有時在研究開始前獲得完全知情同意可能會損害研究的科學價值。例如,在Emotional Contagion中,如果參與者知道研究人員正在進行關於情緒的實驗,那麼這可能會改變他們的行為。在社會研究中,特別是在心理學的實驗室實驗中,從參與者那裡扣留信息甚至欺騙他們並不罕見。如果在研究開始之前無法獲得知情同意,研究人員可以(並且通常會)在研究結束後對參與者進行匯報 。情況匯報通常包括解釋實際發生的事情,糾正任何危害,並在事後獲得同意。然而,關於現場實驗中的匯報是否合適,如果匯報本身可能會傷害參與者,則存在一些爭論(Finn and Jakobsson 2007) 。
第三,有時從受到研究影響的每個人獲得知情同意在邏輯上是不切實際的。例如,想像一位希望研究比特幣區塊鏈的研究人員(比特幣是一種加密貨幣,區塊鍊是所有比特幣交易的公共記錄(Narayanan et al. 2016) )。不幸的是,不可能獲得使用比特幣的所有人的同意,因為其中許多人都是匿名的。在這種情況下,研究人員可以嘗試聯繫比特幣用戶樣本並徵求他們的知情同意。
研究人員可能無法獲得知情同意 - 增加風險,損害研究目標和後勤限制 - 這三個原因並不是研究人員努力獲得知情同意的唯一原因。我建議的解決方案 - 告知公眾有關研究,選擇退出,尋求第三方同意,匯報以及徵求參與者樣本的同意 - 在所有情況下都不可能實現。此外,即使這些替代方案是可能的,它們也可能不足以進行給定的研究。然而,這些例子所表明的是,知情同意並非全部或全部,並且創造性的解決方案可以改善無法從所有受影響方獲得完全知情同意的研究的倫理平衡。
總而言之,研究人員應該,而且可以並且確實遵循更複雜的規則:“對大多數事物採取某種形式的同意。”就原則而言,知情同意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足夠的。尊重人的原則(Humphreys 2015, 102) 。此外,尊重人才只是在考慮研究倫理時需要平衡的原則之一;它不應該自動壓倒慈善,正義和尊重法律和公共利益,這是過去40年倫理學家一再提出的觀點(Gillon 2015, 112–13) 。從道德框架的角度來看,對一切事物的知情同意是一種過於道德的立場,它會成為定時炸彈等情況的犧牲品(見6.5節)。
最後,作為一個實際問題,如果你正在考慮,沒有任何形式的同意做研究,那麼你應該知道,你是在一個灰色地帶。小心。回看道德的說法,研究人員為了進行歧視的實驗研究不同意。是你的理由為強?由於知情同意是中央的許多外行道德理論,你應該知道,你可能會被要求保衛你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