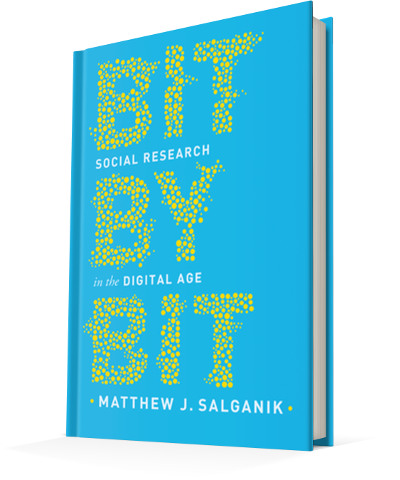6.3數字是不同的
在數字化時代的社會研究都有不同的特點,因此提出了不同的倫理問題。
在模擬時代,大多數社會研究的規模相對有限,並在一套相當明確的規則中運作。數字時代的社會研究是不同的。研究人員 - 通常與公司和政府合作 - 比過去對參與者有更多的權力,關於如何使用這種權力的規則尚不清楚。通過權力,我的意思是簡單地在沒有他們的同意甚至意識的情況下向人們做事的能力。研究人員可以對人們做的事情包括觀察他們的行為並將他們納入實驗。隨著研究人員觀察和擾動的力量不斷增加,關於應該如何使用這種能力的清晰度沒有相應的增加。事實上,研究人員必鬚根據不一致和重疊的規則,法律和規範來決定如何行使權力。這種強大的功能和模糊的指導方針的組合會帶來困難。
研究人員現在擁有的一套權力是能夠在未經他們同意或意識的情況下觀察人們的行為。當然,研究人員可以在過去做到這一點,但在數字時代,規模是完全不同的,這一事實已被許多大數據源粉絲反复宣布。特別是,如果我們從個別學生或教授的規模轉移,而是考慮研究人員日益合作的公司或政府機構的規模 - 潛在的道德問題變得複雜。我認為可以幫助人們想像大規模監視的一個比喻是全景監視器。最初由Jeremy Bentham提出的監獄建築,圓形建築是一個圓形建築,圍繞中央瞭望塔建造了細胞(圖6.3)。佔據這座瞭望塔的人可以觀察房間裡所有人的行為,而不會看到自己。因此,瞭望塔中的人是一位看不見的先知 (Foucault 1995) 。對於一些隱私倡導者來說,數字時代已經把我們帶入了一個全景監獄,科技公司和政府不斷觀察和重述我們的行為。
圖6.3:由Jeremy Bentham首先提出的圓形監獄設計。在中心,有一位看不見的先知可以觀察每個人的行為,但卻無法觀察到。圖片來自Willey Reveley,1791(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
為了進一步推廣這個比喻,當許多社會研究人員考慮數字時代時,他們將自己想像在瞭望塔內,觀察行為並創建一個可用於進行各種令人興奮和重要研究的主數據庫。但是現在,不要想像自己在瞭望塔中,想像自己在一個牢房裡。該主數據庫開始看起來像Paul Ohm (2010)所稱的廢墟數據庫 ,可以以不道德的方式使用。
本書的一些讀者很幸運地生活在那些他們相信他們看不見的先見者負責任地使用他們的數據並保護他們免受敵人攻擊的國家。其他讀者不是那麼幸運,我相信大規模監視提出的問題對他們來說非常清楚。但我相信即使對於幸運的讀者來說,大規模監視仍然存在一個重要的問題: 意外的二次使用 。也就是說,為一個目的而創建的數據庫 - 比如定位廣告 - 有一天可能會用於非常不同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了一個可疑的二次使用的可怕例子,當時政府的人口普查數據被用於促進對猶太人,羅姆人和其他人的種族滅絕(Seltzer and Anderson 2008) 。在和平時期收集數據的統計人員幾乎肯定有良好的意圖,許多公民信任他們負責任地使用數據。但是,當世界發生變化 - 當納粹掌權時 - 這些數據實現了從未預料到的二次使用。很簡單,一旦存在主數據庫,就很難預測誰可以訪問它以及如何使用它。事實上,William Seltzer和Margo Anderson (2008)記錄了18個人口數據系統涉及或可能涉及侵犯人權的案例(表6.1)。此外,正如塞爾策和安德森指出的那樣,這個名單幾乎肯定是低估的,因為大多數濫用都是秘密發生的。
| 地點 | 時間 | 有針對性的個人或團體 | 數據系統 | 侵犯人權或推定國家意圖 |
|---|---|---|---|---|
| 澳大利亞 | 19世紀和20世紀初 | 原住民 | 人口登記 | 強迫遷移,種族滅絕的要素 |
| 中國 | 1966-1976 |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壞階級起源 | 人口登記 | 強迫移民,煽動暴民暴力 |
| 法國 | 1940-44 | 猶太人 | 人口登記,特別普查 | 強迫遷移,種族滅絕 |
| 德國 | 1933-45 | 猶太人,羅姆人和其他人 | 眾多 | 強迫遷移,種族滅絕 |
| 匈牙利 | 1945-46 | 德國國民和報導德語母語的人 | 1941年人口普查 | 強迫遷移 |
| 荷蘭 | 1940-44 | 猶太人和羅姆人 | 人口登記系統 | 強迫遷移,種族滅絕 |
| 挪威 | 一八四五年至1930年 | 薩米斯和克文斯 | 人口普查 | 種族清洗 |
| 挪威 | 1942-44 | 猶太人 | 特別人口普查和擬議的人口登記 | 種族滅絕 |
| 波蘭 | 1939年至1943年 | 猶太人 | 主要是特別普查 | 種族滅絕 |
| 羅馬尼亞 | 1941年至1943年 | 猶太人和羅姆人 | 1941年人口普查 | 強迫遷移,種族滅絕 |
| 盧旺達 | 1994年 | 西人 | 人口登記 | 種族滅絕 |
| 南非 | 1950至93年 | 非洲和“有色”人口 | 1951年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記 | 種族隔離,選民被剝奪權利 |
| 美國 | 19世紀 | 美洲原住民 | 特別普查,人口登記 | 強迫遷移 |
| 美國 | 1917年 | 涉嫌違法的法律草案 | 1910年人口普查 | 調查和起訴那些避免登記的人 |
| 美國 | 1941-45 | 日裔美國人 | 1940年人口普查 | 強迫遷移和拘禁 |
| 美國 | 2001-08 | 疑似恐怖分子 | NCES調查和行政數據 | 調查和起訴國內和國際恐怖分子 |
| 美國 | 2003 | 阿拉伯裔美國人 | 2000年人口普查 | 未知 |
| 蘇聯 | 1919年至1939年 | 少數民族 | 各種人口普查 | 強迫移民,懲罰其他嚴重犯罪 |
普通社會研究人員與通過二次使用參與侵犯人權的行為非常相似。不過,我選擇討論它,因為我認為它會幫助你理解一些人對你工作的反應。讓我們回到Tastes,Ties和Time項目,作為一個例子。通過將來自Facebook的完整和精細數據與來自哈佛的完整和精細數據合併在一起,研究人員創造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豐富的學生社會和文化生活觀(Lewis et al. 2008) 。對於許多社會研究人員來說,這似乎是主數據庫,可以用來做好。但對於其他一些人來說,它看起來像廢墟數據庫的開頭,可能會被不道德地使用。事實上,這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
除了大規模監測之外,研究人員 - 再次與公司和政府合作 - 可以越來越多地干預人們的生活,以便創建隨機對照實驗。例如,在Emotional Contagion中,研究人員在沒有他們同意或意識的情況下在一項實驗中招募了70萬人。正如我在第4章所描述的那樣,參與者進行實驗的這種秘密徵兵並不罕見,並且它不需要大公司的合作。事實上,在第4章中,我教你如何去做。
面對這種增強的力量,研究人員會受到不一致和重疊的規則,法律和規範的製約 。這種不一致的一個原因是數字時代的能力變化比規則,法律和規範更快。例如,自1981年以來,共同規則(管理美國大多數政府資助的研究的一套法規)沒有太大變化。第二個不一致的來源是關於隱私等抽象概念的規範仍在被研究人員積極爭論,政策制定者和活動家。如果這些領域的專家無法達成統一的共識,我們就不應期望實證研究人員或參與者這樣做。不一致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原因是數字時代的研究越來越多地融入其他背景,這導致了可能重疊的規範和規則。例如,Emotional Contagion是Facebook數據科學家與康奈爾大學教授和研究生之間的合作。當時,只要實驗符合Facebook的服務條款,Facebook就可以在沒有第三方監督的情況下進行大型實驗。在康奈爾大學,規範和規則是完全不同的;幾乎所有實驗都必須由康奈爾大學IRB審查。那麼,哪一套規則應該適用於情感傳染-Facebook或康奈爾?當存在不一致和重疊的規則,法律和規範時,即使是善意的研究人員也可能難以做正確的事情。事實上,由於不一致,甚至可能沒有一件正確的事情。
總體而言,這兩個特徵 - 增強的力量和對如何使用這種權力缺乏一致意味著 - 意味著在可預見的未來,在數字時代工作的研究人員將面臨道德挑戰。幸運的是,在處理這些挑戰時,沒有必要從頭開始。相反,研究人員可以從以前開發的道德原則和框架中汲取智慧,這是下兩部分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