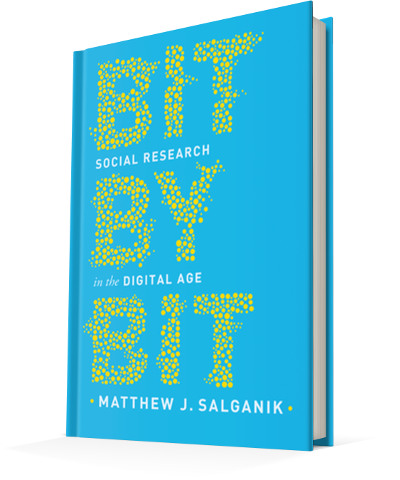历史附录
研究伦理的任何讨论必须承认的是,在过去,研究人员在科学的名义做了可怕的事情。其中最可怕的是塔斯基吉梅毒研究。 1932年,来自美国公共卫生署(PHS)的研究人员招收约400黑人感染梅毒的研究,以监察疾病的影响。这些人从各地塔斯基吉,阿拉巴马州的地区招聘。从一开始,这项研究是不治疗;它被设计为仅记录本病在黑人男性的历史。参与者被欺骗有关的性质研究,他们被告知,这是“坏血”的研究 - 和他们提供虚假和无效的治疗,即使梅毒是一种致命的疾病。随着研究的进展,为梅毒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被开发,但研究人员积极干预,以防止参加者从其他地方得到治疗。例如,在二战期间的科研团队,以防止将已收到的人有他们进入武装部队确保治疗在研究中所有的人deferments草案。研究人员继续欺骗学员,不让他们照顾了40年。这项研究是一项40年临终看护。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发生了反对种族主义和极端不平等的背景下,在美国当时的南部地区很常见。但是,在其40年的历史,该研究涉及几十个研究人员,黑色和白色两种。而且,除了研究人员直接参与,越来越多的必须阅读发表在医学文献研究的15份报告之一(Heller 1972) 。在60年代中期,大约30年后,研究开始,一位名叫罗伯特Buxtun小灵通员工开始小灵通内推来结束这项研究,他认为这在道德上离谱。为了应对Buxtun,1969年小灵通召集了一个小组做研究的完整的伦理审查。令人震惊的是,伦理审查小组决定,研究人员应继续从被感染的人来制定治疗方案。在审议期间,该小组的一名成员甚至说:“你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另一项研究中;利用它“ (Brandt 1978) 。全白色的面板,这是主要是由医生,做了决定,某种形式的知情同意应当收购。但是,专案组判断男人本身不能因为他们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低的提供知情同意。该小组建议,因此,研究人员收到来自当地医疗官员“代孕知情同意”。因此,即使后一个完整的伦理审查,护理扣缴继续。最终,罗伯特Buxtun带着故事的记者,并于1972年让·海勒写了一系列公开的研究,世界报纸上的文章。这之后才是研究终于结束了和护理是提供给谁幸存男子普遍公愤了。
| 日期 | 事件 |
|---|---|
| 1932年 | 约400名男性梅毒在研究中就读;它们不告知研究的性质的 |
| 1937-38 | 小灵通发送移动处理单元面积,但治疗是功不可没的男性在研究 |
| 1942-43 | 小灵通干预,以防止男子被起草了二战,以防止他们接受治疗 |
| 20世纪50年代 | 青霉素成为梅毒广泛使用,有效的治疗;男人仍然没有处理(Brandt 1978) |
| 1969年 | 小灵通召集研究的伦理审查;小组建议,继续研究 |
| 1972年 | 彼得Buxtun,前小灵通的员工,告诉记者有关研究;按打破的故事 |
| 1972 | 美国参议院持有人体实验的听证会,包括塔斯基吉研究 |
| 1973年 | 政府正式结束学习和幸存者授权处理 |
| 1997年 |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公开正式道歉塔斯基吉研究 |
这项研究的受害者不仅包括了399人,而且他们的家庭:至少22个妻子,17个孩子和2个孙子梅毒可能患上本病为治疗扣缴的结果(Yoon 1997) 。此外,造成学习的危害持续长时间结束之后。该研究-名正言顺,降低了非洲裔美国人在医学界的信任,信任受到侵蚀,可能导致非裔美国人,以避免医疗身体健康的威慑(Alsan and Wanamaker 2016)此外,缺乏信任阻碍了努力来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Jones 1993, Ch. 14)
虽然这是很难想象的研究,所以今天可怕的情况发生,我认为有从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三个重要教训人进行了数字化时代的社会研究。首先,它提醒我们,有一些研究认为根本不应该发生的。其次,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研究已经完成研究后,会损害不仅仅是参与者,而且他们的家庭和整个社区长。最后,它表明,研究人员可以做出可怕的道德决策。事实上,我认为它应该引起研究者有些害怕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参与到这项研究中取得了时间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可怕的决定。而且,不幸的是,塔斯基吉绝不是唯一的;有问题的社会和医学研究的其他几个例子在这个时代(Katz, Capron, and Glass 1972; Emanuel et al. 2008)
1974年,为了应对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和研究这些道德的失败,美国国会建立了全国委员会为保护生物医学和行为学研究的人类受试者,并委托委员会制定涉及人类受试者研究的伦理准则。经过四年的贝尔蒙特会议中心会议上,该集团生产的贝尔蒙报告 ,修长而有力的文件,已经对生物伦理既抽象的辩论和研究的日常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贝尔蒙报告有三个部分。在实践与研究 - 贝尔蒙特报告之间的第一部分,边界规定了其职权范围。特别是,它主张的实践 的研究之间的区别,其目的概括性的知识,并且,其中包括每天治疗和活动。此外,它认为,贝尔蒙报告的道德原则只适用于研究。有人认为,研究和实践之间的区别是,贝尔蒙报告是在数字化时代错位的社会研究的一种方法(Metcalf and Crawford 2016; boyd 2016)
贝尔蒙特报告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布置了三个伦理原则,尊重人;善行;与司法和描述如何这些原则在研究实践中应用。这些是我更详细的章节中描述的原理。
贝尔蒙报告设置广泛的目标,但它不是可以很容易地用于监视每天的日常活动的文件。因此,美国政府建立了一套被俗称通用规则的规定(其正式名称是联邦法规第46部分法典第45,一个子部分- D) (Porter and Koski 2008)这些规定描述过程审核,批准和监督研究,它们是机构审查委员会(IRB)的任务是强制执行的规定。要了解贝尔蒙特报告和通用规则之间的差异,考虑如何每个讨论知情同意书的贝尔蒙报告描述了知情同意书,并且将代表知情真正同意广等特点的哲学原因而通用准则列出所需的八个六可选知情同意书的内容。根据法律规定,共同规则管辖,几乎所有的研究,从美国政府获得经费。此外,从美国政府获得资金许多机构通常适用于通用规则对所有的研究在该机构发生的事情,无论资金来源。但是,通用规则不会自动在那个没有从美国政府获得的科研经费公司申请。
我认为,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尊重作为贝尔蒙报告表示伦理研究的广泛目标,但普遍的烦恼与通用规则和伦理委员会工作的过程中(Schrag 2010; Schrag 2011; Hoonaard 2011; Klitzman 2015; King and Sands 2015; Schneider 2015)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伦理委员会的关键不反对道德。相反,他们认为,目前的系统无法取得适当的平衡或通过其他方式能够更好地实现其目标。这一章,但给出将这些伦理委员会。如果您需要遵循一个IRB的规则,那么你应该跟着他们。不过,我建议你考虑你的研究的伦理时也采取以原则为基础的方法。
这种背景很简单总结了我们是如何到达美国IRB审查的规则为基础的系统。当考虑贝尔蒙特报告和通用规则的今天,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是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不同的时代创造的,-相当理智,响应那个时代的问题,在医德特别是违反(Beauchamp 2011)
除了道德努力的医疗和行为科学家创造道德准则,也有更小,更知名的努力,通过计算机科学家。事实上,研究人员第一次运行到由数字化时代的研究产生的伦理挑战不是社会科学家;他们是计算机科学家,研究人员专门从事计算机安全。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计算机安全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些道德有问题的研究,涉及的东西像接管僵尸网络和侵入数千台计算机的弱密码(Bailey, Dittrich, and Kenneally 2013; Dittrich, Carpenter, and Karir 2015)为了应对这些研究中,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土部安全创建一个蓝带委员会编写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研究指导道德框架。这一努力的结果是门洛帕克报告 (Dittrich, Kenneally, and others 2011)虽然计算机安全研究人员所关注的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社会研究者,在门洛帕克报告提供了社会研究者三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首先,门洛帕克报告重申三贝尔蒙特原则,尊重个人,善行和正义,并增加了第四项原则: 法律和尊重公共利益 。我描述了这个第四个原则以及应如何在主章节被应用到社会研究(第6.4.4节)。
二,门洛帕克报告呼吁研究人员能够超越由贝尔蒙报告“的研究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狭义定义移动到更广泛的概念“与人为损害潜在的研究。”贝尔蒙特报告范围的局限性通过喝采很好的说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伦理委员会裁定,安可不是“研究涉及人体”,因此不受通用规则,以检讨。然而,安可显然具有人为伤害的潜力;在最极端的情况,安可可能潜在地导致无辜的人被专制政府被判入狱。 A原则为基础的方法意味着研究者不应该躲在“的研究涉及人类受试者,”即使的IRB允许它的一个狭窄的,法律上的定义。相反,他们应该采取更一般概念“研究与人类伤害的潜力”,他们应该受到大家自己研究与人类伤害的潜在道德考虑。
三,门洛帕克报告呼吁研究人员扩大应用贝尔蒙特原则时所考虑的利益相关者。随着研究已经从生活的一个单独的领域的东西,更嵌入在每天的日常活动感动,伦理方面的考虑必须不仅仅是具体的研究参与者扩大到包括非参与者和所在的研究发生了环境。换句话说,在门洛帕克报告呼吁研究人员,以扩大自己的观点道德领域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参与。
这座历史悠久的附录提供了在社会和医学研究伦理,以及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非常简短的回顾。对于医学研究伦理的书长度治疗,见Emanuel et al. (2008)或Beauchamp and Child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