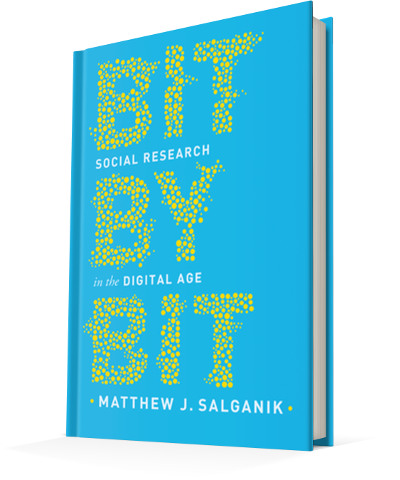6.3数字是不同的
在数字化时代的社会研究都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提出了不同的伦理问题。
在模拟时代,大多数社会研究的规模相对有限,并在一套相当明确的规则中运作。数字时代的社会研究是不同的。研究人员 - 通常与公司和政府合作 - 比过去对参与者有更多的权力,关于如何使用这种权力的规则尚不清楚。通过权力,我的意思是简单地在没有他们的同意甚至意识的情况下向人们做事的能力。研究人员可以对人们做的事情包括观察他们的行为并将他们纳入实验。随着研究人员观察和扰动的力量不断增加,关于应该如何使用这种能力的清晰度没有相应的增加。事实上,研究人员必须根据不一致和重叠的规则,法律和规范来决定如何行使权力。这种强大的功能和模糊的指导方针的组合会带来困难。
研究人员现在拥有的一套权力是能够在未经他们同意或意识的情况下观察人们的行为。当然,研究人员可以在过去做到这一点,但在数字时代,规模是完全不同的,这一事实已被许多大数据源粉丝反复宣布。特别是,如果我们从个别学生或教授的规模转移,而是考虑研究人员日益合作的公司或政府机构的规模 - 潜在的道德问题变得复杂。我认为可以帮助人们想象大规模监视的一个比喻是全景监视器。最初由Jeremy Bentham提出的监狱建筑,圆形建筑是一个圆形建筑,围绕中央了望塔建造了细胞(图6.3)。占据这座了望塔的人可以观察房间里所有人的行为,而不会看到自己。因此,了望塔中的人是一位看不见的先知 (Foucault 1995) 。对于一些隐私倡导者来说,数字时代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景监狱,科技公司和政府不断观察和重述我们的行为。
图6.3:由Jeremy Bentham首先提出的圆形监狱设计。在中心,有一位看不见的先知可以观察每个人的行为,但却无法观察到。图片来自Willey Reveley,1791(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
为了进一步推广这个比喻,当许多社会研究人员考虑数字时代时,他们将自己想象在了望塔内,观察行为并创建一个可用于进行各种令人兴奋和重要研究的主数据库。但是现在,不要想象自己在了望塔中,想象自己在一个牢房里。该主数据库开始看起来像Paul Ohm (2010)所称的废墟数据库 ,可以以不道德的方式使用。
本书的一些读者很幸运地生活在那些他们相信他们看不见的先见者负责任地使用他们的数据并保护他们免受敌人攻击的国家。其他读者不是那么幸运,我相信大规模监视提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非常清楚。但我相信即使对于幸运的读者来说,大规模监视仍然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 意外的二次使用 。也就是说,为一个目的而创建的数据库 - 比如定位广告 - 有一天可能会用于非常不同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一个可疑的二次使用的可怕例子,当时政府的人口普查数据被用于促进对犹太人,罗姆人和其他人的种族灭绝(Seltzer and Anderson 2008) 。在和平时期收集数据的统计人员几乎肯定有良好的意图,许多公民信任他们负责任地使用数据。但是,当世界发生变化 - 当纳粹掌权时 - 这些数据实现了从未预料到的二次使用。很简单,一旦存在主数据库,就很难预测谁可以访问它以及如何使用它。事实上,William Seltzer和Margo Anderson (2008)记录了18个人口数据系统涉及或可能涉及侵犯人权的案例(表6.1)。此外,正如塞尔策和安德森指出的那样,这个名单几乎肯定是低估的,因为大多数滥用都是秘密发生的。
| 地点 | 时间 | 有针对性的个人或团体 | 数据系统 | 侵犯人权或推定国家意图 |
|---|---|---|---|---|
| 澳大利亚 | 19世纪和20世纪初 | 原住民 | 人口登记 | 强迫迁移,种族灭绝的要素 |
| 中国 | 1966-1976 |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坏阶级起源 | 人口登记 | 强迫移民,煽动暴民暴力 |
| 法国 | 1940-44 | 犹太人 | 人口登记,特别普查 | 强迫迁移,种族灭绝 |
| 德国 | 1933-45 | 犹太人,罗姆人和其他人 | 众多 | 强迫迁移,种族灭绝 |
| 匈牙利 | 1945-46 | 德国国民和报道德语母语的人 | 1941年人口普查 | 强迫迁移 |
| 荷兰 | 1940-44 | 犹太人和罗姆人 | 人口登记系统 | 强迫迁移,种族灭绝 |
| 挪威 | 一八四五年至1930年 | 萨米斯和克文斯 | 人口普查 | 种族清洗 |
| 挪威 | 1942-44 | 犹太人 | 特别人口普查和拟议的人口登记 | 种族灭绝 |
| 波兰 | 1939年至1943年 | 犹太人 | 主要是特别普查 | 种族灭绝 |
| 罗马尼亚 | 1941年至1943年 | 犹太人和罗姆人 | 1941年人口普查 | 强迫迁移,种族灭绝 |
| 卢旺达 | 1994年 | 西人 | 人口登记 | 种族灭绝 |
| 南非 | 1950至93年 | 非洲和“有色”人口 | 1951年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记 | 种族隔离,选民被剥夺权利 |
| 美国 | 19世纪 | 美洲原住民 | 特别普查,人口登记 | 强迫迁移 |
| 美国 | 1917年 | 涉嫌违法的法律草案 | 1910年人口普查 | 调查和起诉那些避免登记的人 |
| 美国 | 1941-45 | 日裔美国人 | 1940年人口普查 | 强迫迁移和拘禁 |
| 美国 | 2001-08 | 疑似恐怖分子 | NCES调查和行政数据 | 调查和起诉国内和国际恐怖分子 |
| 美国 | 2003 | 阿拉伯裔美国人 | 2000年人口普查 | 未知 |
| 苏联 | 1919年至1939年 | 少数民族 | 各种人口普查 | 强迫移民,惩罚其他严重犯罪 |
普通社会研究人员与通过二次使用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非常相似。不过,我选择讨论它,因为我认为它会帮助你理解一些人对你工作的反应。让我们回到Tastes,Ties和Time项目,作为一个例子。通过将来自Facebook的完整和精细数据与来自哈佛的完整和精细数据合并在一起,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丰富的学生社会和文化生活观(Lewis et al. 2008) 。对于许多社会研究人员来说,这似乎是主数据库,可以用来做好。但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它看起来像废墟数据库的开头,可能会被不道德地使用。事实上,这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除了大规模监测之外,研究人员 - 再次与公司和政府合作 - 可以越来越多地干预人们的生活,以便创建随机对照实验。例如,在Emotional Contagion中,研究人员在没有他们同意或意识的情况下在一项实验中招募了70万人。正如我在第4章所描述的那样,参与者进行实验的这种秘密征兵并不罕见,并且它不需要大公司的合作。事实上,在第4章中,我教你如何去做。
面对这种增强的力量,研究人员会受到不一致和重叠的规则,法律和规范的制约 。这种不一致的一个原因是数字时代的能力变化比规则,法律和规范更快。例如,自1981年以来,共同规则(管理美国大多数政府资助的研究的一套法规)没有太大变化。第二个不一致的来源是关于隐私等抽象概念的规范仍在被研究人员积极争论,政策制定者和活动家。如果这些领域的专家无法达成统一的共识,我们就不应期望实证研究人员或参与者这样做。不一致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是数字时代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融入其他背景,这导致了可能重叠的规范和规则。例如,Emotional Contagion是Facebook数据科学家与康奈尔大学教授和研究生之间的合作。当时,只要实验符合Facebook的服务条款,Facebook就可以在没有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大型实验。在康奈尔大学,规范和规则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所有实验都必须由康奈尔大学IRB审查。那么,哪一套规则应该适用于情感传染-Facebook或康奈尔?当存在不一致和重叠的规则,法律和规范时,即使是善意的研究人员也可能难以做正确的事情。事实上,由于不一致,甚至可能没有一件正确的事情。
总体而言,这两个特征 - 增强的力量和对如何使用这种权力缺乏一致意味着 - 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在数字时代工作的研究人员将面临道德挑战。幸运的是,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没有必要从头开始。相反,研究人员可以从以前开发的道德原则和框架中汲取智慧,这是下两部分的主题。